
Marlan Scully教授 图片来自 TEXAS A&M UNIVERSITY官网
编者按:
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Marlan Scully教授,是量子光学领域的先驱科学家。在激光物理和量子光学领域,他作出了多项突破性发现,包括:与Willis Lamb合作提出了激光的量子理论(Scully-Lamb量子理论),实现了无粒子数反转激光的首次实验演示,首次成功在热原子气体中产生超慢光,以及利用量子相干性实时检测炭疽病毒等。Marlan Scully教授科研兴趣浓厚广泛,著作等身,他合作编写了量子光学的经典教科书Quantum Optics和Laser Physics。除了过人的科学造诣,他还是活跃的领导者,例如每年在犹他州盐湖城Snowbird举行的 Winter Colloquium on the Physics of Quantum Electronics(简称PQE),他从创始初期就负责领导,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物理学家。
——Photonics Research主编 杨兰
Marlan Scully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会士;曾获中科院“爱因斯坦教授”称号。因其杰出工作,他荣获了许多重要奖项,包括 APS Schawlow奖、OSA Townes奖、 IEEE Quantum Electronics奖、富兰克林学会Elliott Cresson奖章、 OSA Lomb 奖和OSA DPG Herbert Walther 奖等。
近期,Marlan Scully教授接受了Photonics Research 主编杨兰教授的专访,畅谈他与量子光学科研事业的缘起、回顾他的几项重要研究进展、探讨当今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发展方向。

(经典量子光学教材Quantum Optics图片来自谷歌图片)
杨兰: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已有几十年,您最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领域?
Marlan Scully:我在怀俄明大学获得量子力学专业的学士学位后,便到耶鲁大学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从事低温物理方面的工作。而著名物理学家Willis Lamb当时也在耶鲁,正是他发现了兰姆移位,并将量子电动力学发展成一个兼具理论与实验的研究领域。我非常幸运地为Willis Lamb所教授的量子力学课程批改作业。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低温物理并不是一门容易的学科。幸运的是,那时激光研究逐渐兴起,Lamb在耶鲁大学研究激光,当时他建议我一起研究激光的基本原理,研究激光密度矩阵如何从阈值下过渡到阈值上。他说朱利安·施温格曾经就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结论。其实我当时不太愿意,但他坚持建议我尝试一下,表示这个课题足够一篇毕业论文了。自那之后,我便进入了这一领域,现在看来,我非常幸运遇到了Willis Lamb,并且有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就是我进入量子光学领域的原因:好运,以及优秀的共事者。

Marlan Scully(中间)和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Willis Lamb(右二),Olga Kochakovskaya(右一),Ali Javan(左一)及Paul Mandel(左二),来自www.lambaward.org
杨兰:在您看来,量子光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或突破是什么呢?
Marlan Scully:量子光学对人类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激光的发现,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1960年我还在求学,那时尽管光学领域出现了许多小而有趣的方向,比如法布里-珀罗腔、光谱学等,但总体来说光学并非是热门领域。直到激光出现之后,各种光谱学研究才成为了可能。例如拉曼光谱学,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在量子力学诞生之前,在1924年由理论物理学家Smekal提出的。该理论是指当入射光被振动的分子散射时,会产生频率稍低的散射光,这种出射光的频率下移被称为“斯托克斯散射”。当拉曼首次进行实验时,他使用的是阳光,而100亿个光子中只有1个能产生拉曼位移,数量太少了;但是如果使用激光,将会得到较强的信号。
加拿大的Boris Stoicheff等人是推动激光拉曼光谱应用的先驱者。Stoicheff去印度时,他的光谱图像就留在了拉曼的墙上。足以看出,激光的出现开拓了整个光学领域(如非线性光学,量子光学,激光光谱学等)的发展。至今,光学领域的版图已经如此宏伟。
杨兰: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激光理论被提出时的故事吗?
Marlan Scully:在1905年,爱因斯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深刻诠释了统计力学。那时麦克斯韦的电磁波动方程仍被广泛认可,爱因斯坦和其他人也都还没想到光子的概念。从普朗克对热辐射熵研究的方法中得到启发,爱因斯坦意识到热力学概念中光的熵是由两部分组成,光具有双重特性,既有波的特性,也有粒子的特性。正是通过研究波动和光的统计特性,才使爱因斯坦提出了光子的概念。
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开始研究高强度激光问题。Glauber等人证明描述一个相干辐射源的密度矩阵非常简单,即光子的泊松统计分布,这就是现在所说的Glauber相干态。无线电波是Glauber相干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激光的辐射密度矩阵该如何表示?在低于阈值的情况,爱因斯坦已经从热力学角度给出了解释;而高于阈值时是相干的,Glauber也给出了解释。但在Glauber给出解释之前,我们并不清楚。在他著名的关于激光辐射的讲座中,Glauber说道:“要想构建密度算符,只能通过分析和求解问题,以反推密度算符。”他说在谐振腔的情况下,可推算出公式。“非线性对于激光场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在这一问题有进展之前,不太可能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解释激光的频率带宽及其输出波动。”这是Glauber 1964年讲话中的内容。
当时,Lamb将这一问题抛给了我,幸好我还没看过Glauber的论述,否则我可能会退却。那年整个夏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Lamb回来后,我们才发现激光辐射的密度矩阵的确可以通过分析激光固有的非线性表示出来。

Marlan Scully和Willis Lamb、Murray Sargent合著的教材《Laser Physics》图片来自谷歌图片
杨兰:激光是您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喜欢哪个问题、对哪项成果感到最振奋?
Marlan Scully: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是一种弱耦合气体,其原子服从玻色统计。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完成了这一实验,随后麻省理工学院的Daniel Kleppner教授对此作出了总结,并成功吸引了一大批人研究这一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可能,认为得到的只是一团低温气体。氦原子成功实现凝聚态的原因在于其存在零点涨落,但如果把铷这样的大原子与另一个大原子放在一起,它们将发生极化,变成一团。幸运的是,我们错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确实存在。后来,Dan Kleppner在Physics Toda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与激光相似,是发生在原子之间的协同现象。这类物理现象与激光类似,因此称其为原子激光。
随后,Lamb打电话对我说:“简直太疯狂了,你去证明一下这是错误的。思路是证明这些弱相互作用的原子并不具有非线性,这些原子并不会产生类似光子般的非线性,因为光子是通过增益介质相互作用的。你要证明这些全都不对!”我当时赞同他的观点,于是我开始进行证明,这一问题逐渐吸引了我。然而,几个月后我发现,他们的结果竟然是正确的!
借助一个合理的模型和细致的推导,我得到了相同的波动方程以及跟接近阈值的氦氖激光相同的密度矩阵表达式。最终推导出的方程与激光的量子理论的数学结果完全一致。我既震惊又兴奋,马上打电话给Lamb:“Kleppner是正确的,这就是原子激光!”Lamb很激动:“不可能!你尽快把计算结果寄给我看看。”我写下来并寄给了他。他回复道:“尽管我还没有论据证明这是错的,但我就是不喜欢这个结果!”
之后,我把计算过程写成论文手稿,署上他的名字寄给了他。他拍打着我的头和肩膀:“不,我绝对不会和你一起发表这个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糟糕,我对这一结果非常不满意!”我只好说:“Willis,保持一段长达四十年的友谊的唯一方法就是与朋友一起并肩跋涉,克服困难。你并没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你有我,你想怎么样?迫使我疏远你吗?”当然,我是在和他开玩笑。Lamb无奈道:“好吧,既然你很确定这一结果是正确的,那就发表吧,但是不要署我的名字,我们仍然是朋友。”于是,我发表了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人们在实验中仍旧观察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原子激光的波动与光子激光完全一致,这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现在这个理论被应用在生物物理领域,即我们熟知的生物光子学。[Herbert] Fröhlich是超导研究的开拓者,他在1950年第一个指出了电声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之后Bardeen、Cooper和Schrieffer据此得出了BCS理论。这些研究者们奠定研究基础的过程非常有趣。当时他还说过,在生物体中,也极有可能存在相干现象,或者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多年来,我几乎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华盛顿的Bin-Solomon博士推动了这一研究。目前我们已经对蛋白质分子的纵向振动模式进行了计算;与激光相同,它也遵循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研究超流体和玻色凝聚等,是一种真正的乐趣,是一个真正把乐趣和实验相结合的领域。

Marlan Scully在得克萨斯A&M大学的超快激光实验室
杨兰:除了在量子光学领域,您还发表过利用飞秒自适应光谱技术检测炭疽孢子的文章,您研究这一方向的动机是什么呢,能否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
Marlan Scully:如何解决本领域内以及领域外的其他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一直鼓励学生们平等对待应用物理和基础物理方面的研究。
故事回溯到2001年左右,普林斯顿炭疽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生物恐怖袭击事件,2001年9月18日开始,有人将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了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此事件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开始之初,我们需要一种远快于实验室湿法化学的分析技术,来检测邮件上的白色粉末是否是炭疽孢子。
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并决定尝试拉曼光谱技术,但拉曼光谱信号仍然非常弱。而采用相干拉曼光谱技术——可以这样理解“相干”:假设有部分邮件样本中的分子,比方说有一小份一万万兆(即1020)个分子,如果能够协同这些分子的行为,使其相干振荡,那么信号强度将翻倍。普通拉曼的信号强度与每毫升中的原子数n成正比,而相干反斯托克斯拉曼光谱信号强度则与n2成正比,因此相对于拉曼光谱技术更优。
然而问题在于,采用非寻常相干拉曼技术——之所以说“非寻常”是因为相比普通拉曼技术,信号强度变成了n2,这是好的一方面;而坏的一方面则是噪音也变成了n2,因此造成了信号和噪音的混淆。所以我开始着手研究改进这项技术的方法,最终想到了飞秒自适应技术——我们称之为飞秒自适应光谱技术FAST CARS(Femtosecond adaptive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for coherent anti-Stokes Raman spectroscopy, FAST CARS)【译注1】,结果证明这一技术有望实现检测目标。
于是我前往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向他们展示了这一技术的可能性。他们回复说这一技术不可行,但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拨付了一百万经费让我们研究其不可行的原因。我回到得克萨斯,决定与其他人一起向研究计划局证明这项技术的可行性。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前往研究计划局,他们回复说:“太好了,这里是1000万,拿去做实验吧”。然而,实验需要用到飞秒激光器,但我们手中并没有。事实上,21世纪初期,仅在密歇根和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才有飞秒激光器。由于我认识很多同行,所以我给普林斯顿的朋友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他们说,有很多人都想用飞秒激光器,但只有普林斯顿的教师才有资格使用激光器。除非你来我们这里做访问教授,这件事才有得谈。
于是,我去参加了“面试”,展示了我们的技术设想。然而,坐在房间后面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喊道:“这不可能,你错了!众所周知用CARS不行,因为CARS同时也会放大噪声……”毕竟我还想借他们的激光器一用,所以我并没有和他争论。我说:“我一直希望对我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朋友的私下告诫,而非敌人公然的针对。”他回复道:“这个房间里足足有200人,所以这不算私下场合;而且我们也不是你的朋友。”
(大笑)我继续讲我的报告,只好告诉他:“你错了,原因如下…”我解释了原因,之后他又和我持续争论了一个星期,最后他终于相信了我的理论。于是,我们在普林斯顿和得克萨斯A&M大学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学习如何使用、搭建这类激光器。我的朋友——得克萨斯A&M大学的Alexei Sokolov和一些聪明的学生们一起,在普林斯顿的科学家之前就实现了这一技术。
我们起初的目标是在扫过一封信的时间(1 ms~10 ms内)进行检测,经过多次试验,最终成功实现了FAST CARS技术,能够在短至1 ns~1μs内检测到炭疽病毒。FAST CARS技术的这一成功应用,让我们开始探索拉曼光谱在病毒检测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有幸与德国的同事合作进行病毒检测研究,一位名叫Volker Deckert的同事和我们一起想出了许多应用这一技术的好点子。实际上,我们成功实现了快速检测的目标,并提高了分辨率【译注2】。他建议将这一技术命名为“FASTER CARS”。
借助该技术,如今我们能检测到单个COVID-19病毒,并用针尖增强拉曼光谱扫描成像。针尖增强拉曼光谱是另一个专业术语,这项技术用一个如同原子力显微镜那样的微小针尖扫描物体表面,对表面氨基酸进行拉曼光谱成像。我们利用这一技术也实现了很高的分辨率。这就是我们实验室所进行的炭疽、COVID-19的病毒检测研究。

细菌孢子的快速成像 图片来自www.pnas.org
杨兰:您可否谈一谈您当前的研究兴趣?
Marlan Scully:疫情之前,我正在研究由David Lee提出的一个问题,David Lee因发现氦-3的超流体获得了诺贝尔奖。David曾经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在他离开康奈尔大学之后,我幸运地聘请他到了得州A&M大学——亦被戏称“得州原子(Atomic)与分子(Molecular)大学”。有一天David问我,为什么黑洞的霍金熵与其面积而非其体积成正比?我翻遍教科书都没找到想要的答案,所以我尝试用另一种理论解释:Unruh辐射。Bill Unruh是一位伟人,他在霍金之后,给出了一种有关黑洞辐射的深刻见解,发表了一些著作等。借助Bill的理论,我想出了一种理解黑洞辐射的新方法,即观察原子落入黑洞时所发出的光。我对此非常着迷,并打电话给Bill告诉他我的研究,他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工作了一年,如今加入了我们部门。
新冠疫情过去后,我们将继续这项研究。这是我感兴趣的方向之一,如果我能从业余挤出更多时间,我想在这方面做更多工作,研究量子光学、压缩光与黑洞Hawking-Uhruh辐射之间的深层联系。量子光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能够为其它学科做出贡献,能在更深层面上诸如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物理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但目前我仍在继续新冠肺炎这方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远距离成像的需求在量子光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远距离的植物健康和活力的(检测)成像也是量子光学科学家在农业科学中浓厚兴趣点之一【1,3】;我们在 Photonics Research 发表的文章Enhanced four-wave mixing process near the excitonic resonances of bulk MoS2中有具体报道。同时,我们也对潘建伟院士团队去年在 Photonics Research 发表的文章Single-photon computational 3D imaging at 45 km十分感兴趣,下图是他们团队进行单光子成像的示意图;他们的结果让我们感到振奋,这也应验了那句老话: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事实上,单光子远距成像技术还有望广泛应用于农业【2】。

Marlan Scully与潘建伟院士

在白天远程拍摄超过21.6公里的目标物。(a) 实验的整体示意图;(b) 目标物(建筑K11)的地面实况图像;(c) 在可见波段,用标准天文相机拍摄的目标物图像;(d)–(g) 在日光下使用单光子激光雷达拍摄的深度剖面,并通过不同的算法应用于1.2 PPP(photon per pixel,每个像素点的光子数)和SBR=0.11(signal-to-background ratio,信号-背景比)的数据进行图像重构:(d) 用像素极大似然法重构;(e) 用高效光子算法重构【4】;(f) 用Rapp和Goyal 【5】的算法重构;(g) 用所提的算法重构。通过将重构的图像与使用大量光子获得的高质量图像进行比较来计算峰值信噪比 (PSNR)。
杨兰:请问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提出很有意义的问题呢?
Marlan Scully:首先,选择很有前景的领域,比如量子生物学,这是一个借助FAST CARS和FASTER CARS等激光光谱技术,也是一个将量子光学技术应用在生物学领域的学科,如对冠肺炎病毒表面的氨基酸进行成像等。其次,反复斟酌一些深层的问题,比如之前的问题: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与激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通过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能否发现一些有趣的、意想不到的结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认为首位真正在哲学意义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是Roger Penrose。由于在黑洞物理方面突破性的贡献,他获得了2020年的诺贝尔奖。他问道,量子计算机是否有可能模拟大脑工作的部分原理?每个人都回答,应该不可能,大脑中的温度太高,因此不存在相关性。在他的精彩著作The emperor's new mind中,Penrose写道:“好吧,也许你们说的是对的,但一切都尚未盖棺定论。”所以要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我现在就对Penrose的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比如能否用超辐射等现象中的量子相干和纠缠,来解释生物学知识?大脑中是否存在量子的活动?
杨兰:您发起的量子电子学物理冬季研讨会(PQE)已成功举办了50多年,促使您持续举办这一研讨会的原因是什么?
Marlan Scully:当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我曾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阿尔伯克基的柯特兰激光实验室的研究者们共事,他们都很擅长滑雪。当时他们正打算学习光学和量子技术,于是他们说,如果能在犹他这种有一个开放坡道的新兴滑雪胜地举办会议,早上去参加会议、下午滑雪,晚上回来继续参加会议,那该多好啊!所以我们发起了PQE。
这一研讨会非常受欢迎,一是因为有趣,二是因为这是一种绝妙的研讨交流方式。在早上8点到11点半的讲座之后,听众们已经开始感到疲惫;如果这时去滑雪,你也许能在滑雪缆车上偶遇Julian Schwinger等人。这也是PQE活动的亮点,提供了一个与Julian Schwinger等大牛轻松交谈的氛围,一个在友好、美妙的环境中辩论的机会。
我们将PQE会议持续办了下去,50年后的今天仍在继续。量子电动力学领域如今成果丰硕,许多参加研讨会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很多人现在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年复一年,参加该会议的人们组成了一个社群、一个家庭。目前PQE大约有300名成员,他们以一种特殊的途径相互了解——一种不同于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物理学会会议上简单碰面的途径。
杨兰:除了组织PQE会议,您同时还兼任许多国际学术委员会以及评奖委员会的成员,您热心帮助服务社区和学术界的初衷和收获是什么?
Marlan Scully:和其他人一样,我倾向于关注有趣且简单的科研工作,遗憾有时候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关心年轻的同事。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Dudley Herschbach是一位伟大的化学物理学家,已经在我们部门工作了十几年,总是在四处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在抽时间编辑期刊。多么令人钦佩啊,我永远无法像他一样。
但我确实在努力帮助年轻同事和学生,这非常令人振奋。比如Wolfgang Schleich,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德国的时候,他曾是我的博士生。如今他已经成功地从联邦政府那里为德国各地大学的研究人员争取了7亿欧元的经费。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对此也感到非常激动。我想说的是,要时刻注意你能为同事做些什么,因为你将从中得到巨大的快乐。耶稣说过,“拯救自身的方法就是丧掉生命”,要用你的一生去帮助别人。
杨兰:您在工作之余的爱好是什么呢?您又被称为“量子牛仔”,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Marlan Scully:我在怀俄明一个偏远农场中长大,喜欢爬山,包括攀爬魔鬼塔和怀俄明其他山峰。耶鲁有一个非常棒的登山俱乐部,David Lee也是其中一员。钓鱼、放牧都是我一直喜欢的活动。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时,我有点过于敢作敢为、有冲劲,以至于有人说:“Scully的做事风格就像那些’先开火再问话’的西部牛仔一样”。我做事率真有冲劲的风格为人所知,再加上我的确有几个农场,我想这大概是我被称为“牛仔”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Marlan Scully 和Vladilen Letokhov在"ℏ"农场。图片来自Marlan Scully.
杨兰:您对计划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们有哪些建议?
Marlan Scully:首先,找到一个真正吸引你的问题。对于量子光学来说,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纠缠,或者利用压缩光实现性能更优的显微成像等。这些问题,一方面属于基础科学,另一方面,它们其实有实际应用。无论你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什么,都要思考如何有效利用那些技术的优势,让自己有所收获。
以我自身为例,我研究激光,当我发现激光陀螺仪在工业中的应用潜力时,数十年来我一直为激光陀螺仪应用方面提供建议。尽管我对此并非特别感兴趣,这也并不是我的首要研究方向,然而一旦开始研究,它便会吸引我继续做下去。因此一定要钻研那些你真正喜欢的、让你有探索欲的问题。
Webinar完整版视频回放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宇翱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袁璐琦教授、得克萨斯A&M大学易震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译注:
【1】文章见 Scully, M. O. et al "FAST CARS:Engineering a laser spectroscopic technique for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l spor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17 (2002):10994-11001. Web. 11 July. 2021
【2】文章见 Volker Deckert, Tanja Deckert-Gaudig, Dana Cialla-May, Jürgen Popp, Roland Zell, Stefanie Deinhard-Emmer, Alexei V. Sokolov, Zhenhuan Yi, and Marlan O. Scully, "Laser spectroscopic technique for direct identification of a single virus I:FASTER CA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 (45), 27820-27824 (2020).
Alexei V. Sokolov, Volker Deckert, Zhenhuan Yi, Marlan O Scully, "Detecting coronavirus with FASTER CARS:molecular coherence at work," Proc. SPIE 11700, Optical and Quantum Sensing and Precision Metrology, 117003G (5 March 2021); https://doi.org/10.1117/12.2586828
文献:
【1】Brian A. Ko, Alexei V. Sokolov, Marlan O. Scully, et al. Enhanced four-wave mixing process near the excitonic resonances of bulk MoS2[J]. Photonics Research, 2019, 7(3):03000251
【2】Zheng-Ping Li, Xin Huang, Yuan Cao, et al. Single-photon computational 3D imaging at 45 km[J]. Photonics Research, 2020, 8(9):09001532
【3】Zhang, L., G. S. Agarwal, and M. O. Scully. "Beam Focusing and Reduction of Quantum Uncertainty in Width at the Few-Photon Level via Multi-Spatial-Mode Squeezing." PhRvL 122(2019).
【4】D. Shin, A. Kirmani, V. K. Goyal, and J. H. Shapiro, “Photon-efficient computational 3-D and reflectivity imaging with single-photon detectors,” IEEE Trans. Comput. Imaging 1, 112-125 (2015).
【5】J. Rapp and V. K. Goyal, “A few photons among many:unmixing signal and noise for photon-efficient active imaging,” IEEE Trans. Comput. Imaging 3, 445-459 (2017).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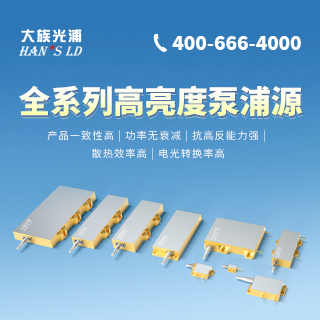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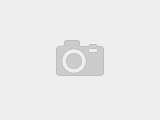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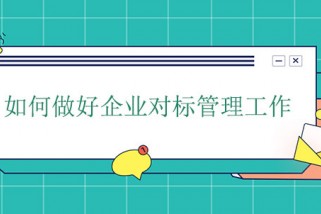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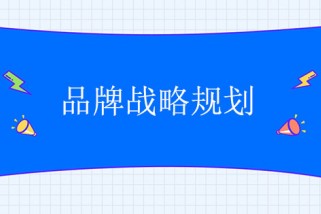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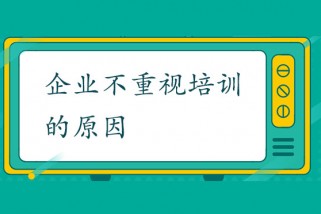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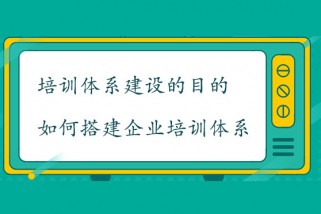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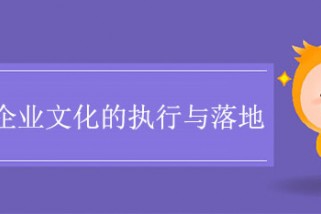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