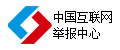摘要
激光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其中在空间维度实现局域化的微型化激光成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石。文章将从光辐射是由辐射源和其所处的辐射环境共同决定的这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基本观点出发,简述激光微型化的相关背景、物理意义、发展脉络,并讨论微型化激光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真空零点能,珀塞尔效应,激光微型化,微纳激光,等离激元纳米激光
01
真空光子态在光辐射中的重要作用与激光微型化
光辐射是由辐射源和其所处的辐射环境共同决定的,对这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基本观点的深刻理解推动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从黑体辐射普朗克定律到费米黄金法则,再到珀塞尔效应与腔量子电动力学,真空光子态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图1)。

图1 真空光子态在光辐射中具有重要作用。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中的
是真空光子态密度;费米黄金法则中的ρ(v)为光子态密度;光学腔中的光子态密
与真空光子态密度
的比值给出了辐射速率增强的珀塞尔因子
1900年普朗克给出了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
其中S(ν)是黑体单位频率间隔内辐射的能量密度;
是真空光子态密度,可通过计算一个边长远大于自由空间波长的立方体腔的态密度来获得;hv是单个光子的能量;
是玻色—爱因斯坦统计给出的在能量hv上占据的光子数。光量子假说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而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是在1924年提出的,尽管这些概念在1900年还不存在,但普朗克定律本身表明真空光子态在光辐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16年,爱因斯坦通过研究热平衡下辐射体吸收与辐射之间的关系,简洁明确地推导出了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并揭示出了一种新的辐射机制——受激辐射,同时他给出了受激辐射系数与自发辐射系数之间的关系[1]。受激辐射为激光的发明奠定了基础。对自发辐射的深入理解在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激光发明之后,对自发辐射的深入理解也揭示了激光微型化的重要意义,持续推动了微纳激光的发展。
1946年,珀塞尔(E. M. Purcell)指出通过将原子与腔耦合可以改变其自发辐射的速率[2]。珀塞尔当时在研究核磁共振现象,他预测在谐振结构(例如谐振电路)中,原子的自发辐射速率可以被显著地加快。珀塞尔利用费米黄金法则计算了自发辐射速率并解释了增强效应。一个辐射源从初始态
到最终态
的自发辐射速率γ可由费米黄金法则计算得到:

其中τsp是辐射源的自发辐射寿命,H是辐射源—光子态相互作用哈密顿量,ρ(v)是光子态密度,这里H的矩阵元是体积归一化的。在真空中,ρ(v)是
。在有限大小的腔体中,光子态密度从连续变为离散,对于某个光子态(腔模),光子态密度为
,其中∆v=v/Q,Q和Vm是该光子态的品质因子和模式体积。在弱耦合情况下,
与
的比值给出了自发辐射速率的珀塞尔增强因子。
1947年,兰姆(W. E. Lamb Jr.)实验上发现了氢原子2S1/2和2P1/2能级之间由于真空光子态的零点能所引起的劈裂(兰姆位移)[3]。兰姆位移的发现揭示了真空零点能对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重要影响,推动了量子电动力学的发展。
对真空光子态在光辐射中的作用的进一步深刻理解开启了腔量子电动力学领域。早期的工作包括H. B. G. Casimir和D. Polder在1948年对原子和腔相互作用能的研究[4],以及E. T. Jaynes和F. W. Cummings在1963年对辐射源和高品质因子光腔之间强耦合现象的研究[5]。K. H. Drexhage等人在1966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工作,观察到稀土离子荧光寿命可被金属薄膜调制的现象[6]。1981年,D. Kleppner指出光子态密度的改变不仅可以增强自发辐射还可以抑制自发辐射[7]。为了实现抑制效应,他提出了将辐射源与低于截止频率的波导耦合的方案。低于截止频率时,波导的态密度远小于自由空间的光子态密度,因此可以大幅度地抑制自发辐射。
1983年,P. Goy等在里德伯原子与毫米波光腔耦合系统中观察到了腔增强的单原子自发辐射[8]。1985年,G. Gabrielse和H. Dehmelt在里德伯原子与微波腔的耦合系统中观察到了自发辐射被抑制的现象[9]。不久之后,光波段下的自发辐射调制在原子—光学腔耦合系统中被成功实现[10,11]。辐射源—光腔耦合腔量子电动力学系统的发展使得测量和操控单个光子的量子特性成为可能,相关研究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由于自发辐射在发光二极管、激光、光电探测器和太阳能电池等半导体光电器件中起着关键作用,固态系统中自发辐射的调控也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12—15]。
在1990年前后,人们发现激光的阈值和调制速率会受到激光尺寸的影响[16—19]。首先,微型化激光具有更小的增益材料体积和更大的自发辐射耦合因子,因此其阈值可以更低。同时,微型化激光具有更快的自发辐射以及受激辐射速率,因此其调制速率更快。自那时起,实现体积更小、阈值功耗更低、调制速率更快的微型化激光一直是相关领域研究的焦点。
02
激光微型化:从微波激射器、激光到表面等离激元纳米激光
2.1 微波激射器
1954年,J. P. Gordon,H. J. Zeiger和C. H. Townes实现了微波激射器(microwave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Maser)[20]。他们利用处于激发态的氨分子作为增益介质,并使用约12 cm长的微波腔提供反馈,实现了波长约为12.56 cm的微波激射(图2(a))。1958年,A. L. Schawlow和C. H. Townes提出了以钾蒸汽作为增益介质实现红外和可见光波段微波激射器(infrared and optical Masers)的设想[21]。由于红外和可见光波段的波长比微波小得多,受到微纳加工能力的限制,那时几乎不可能实现腔长与激光波长同量级的激光,他们提出利用厘米级光学腔的高阶模式来实现激射。

图2 激光微型化之路 (a)微波激射器(Maser)[20];(b)激光(Laser)[22];(c)等离激元纳米激光(Spaser,亦称plasmonic nanolaser)[33—35]
2.2 激光
1960年,T. H. Maiman首次实现了激光(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Laser)[22]。他使用一根约1 cm长的红宝石棒作为增益介质,在其两端覆盖银作为反射镜提供光反馈,在闪光灯的激发下实现了波长为694.3 nm的激光输出(图2(b))。Maiman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利用激光探索世界的时代,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与1954年发明的微波激射器相比,Maiman发明的激光的出射光束频率高出了超过5个数量级。频率的提升大大增加了信息带宽,使得高速光纤通信得以实现。激光的高工作频率也意味着可以将光斑聚焦到更小尺度从而实现更高的光功率密度。在同样聚焦到衍射极限光斑的情况下,激光的聚焦光斑要比微波激射器的小10亿倍以上。极高的光功率密度使得激光驱动的核聚变成为可能。此外,光学器件的特征尺寸受到衍射极限的限制,高工作频率使得相干光源的尺寸以及相关光学器件(如波导、调制器和光探测器)的尺寸可以显著缩小。
1962年,基于同质结的半导体激光被实现[23—26]。1963年,H. Kroemer和Z. Alferov分别提出了利用半导体双异质结构建激光的设想[27,28]。双异质结结构是实现高性能半导体激光的关键,因为双异质结结构不仅可以提供高效的载流子注入,同时其可以将注入的载流子和激光模场限制于有源区。
半导体激光的发明为现代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当前,被广泛应用的微型化半导体激光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边发射激光(edge emitting laser,EEL),多采用周期光栅形成分布式反馈(DFB)。边发射激光的特征尺寸约在100个真空波长量级,是远距离光纤通信的核心光源。第二种是面发射激光(surface emitting laser,SEL)。商业化的面发射激光使用两个分布式布拉格反射镜(DBR)在垂直方向上提供腔反馈。DBR镜片由外延生长的折射率交替变化的多层介质材料组成。面发射可以将激光特征尺度降至10个真空波长量级,相较边发射激光具有更低的能耗,是短距离数据通信和消费电子产品最核心的光源。

图3 可将激光的特征尺寸缩小到一个真空波长量级的微盘激光(a)[29]、光子晶体缺陷态激光(b)[30]和纳米线激光(c)[31]
在世纪之交,包括微盘激光、光子晶体缺陷态激光和纳米线激光在内的半导体微纳激光的发明将激光的特征尺寸缩小到一个真空波长量级(图3)。微盘激光于1992年首次实现,利用微盘中的光学回音壁模式实现腔反馈[29]。光子晶体缺陷态激光于1999年首次实现,利用二维光子晶体中的点缺陷模式进行光场限制和反馈[30]。半导体纳米线激光于2001年首次实现,利用纳米线两个端面作为反射镜形成法布里—珀罗式的腔反馈[31]。
2.3 等离激元纳米激光
在激光中,增益介质通过受激辐射放大光子,因而激光尺寸受光学衍射极限限制,最小尺度在波长量级(对可见光来说,大约几百纳米)。为了突破光学衍射极限,获得体积更小的激光,D. J. Bergman和M. I. Stockman在2003年提出了等离激元纳米激光(surface plasmon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Spaser,亦称plasmonic nanolaser)的概念[32]。
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由等离激元谐振腔和增益材料组成,其工作原理包括增益材料的激发和等离激元的辐射和放大的过程。在外界提供的泵浦能量激发下,增益材料产生粒子数反转,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向低能级跃迁并辐射至等离激元模式,该模式再经由增益材料的受激辐射放大形成等离激元激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通过受激辐射放大等离激元而非放大光子突破光学衍射极限,其谐振腔特征尺度可降至真空波长的十分之一量级,达到电子器件特征尺度(图4)。

图4 等离激元纳米激光通过受激辐射放大等离激元(a)而非放大光子(b)突破光学衍射极限
2009年,国际上三个团队首次实现了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图2(c))。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翔研究组和北京大学戴伦研究组合作,实现了基于一维半导体纳米线—绝缘体—金属结构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图5(a))[33];埃因霍温理工大学M. T. Hill研究组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宁存政研究组等合作,实现了基于金属—半导体—金属三层平板结构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图5(b))[34];诺福克州立大学M. A. Noginov研究组与普渡大学V. M. Shalaev研究组等合作,实现了基于局域表面等离激元共振的金属核—内嵌增益介质壳的核—壳结构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图5(c))[35]。2011年,张翔研究组报导了室温半导体等离激元纳米激光[36]。如今,光场限制从一维到三维、激射波长从紫外到近红外的各类型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及其阵列被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国的科研机构在实验上成功实现。对于纳米激光近年来的发展有许多优秀而全面的综述,可参见参考文献[37—51]。

图5 2009年首次实现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所采用的共振腔模式 (a)纳米线—绝缘体—金属间隙等离激元模式[33];(b)金属—半导体—金属三层平板结构等离激元模式[34];(c)金属核—内嵌增益介质壳的核—壳结构等离激元模式[35]。其中,左侧是三维结构示意图,右侧是亚衍射极限模式场分布图
03
等离激元效应能否提高激光性能?
等离激元效应通过耦合光场与自由电子振荡可以实现突破光学衍射极限的光场限制,然而其利用的自由电子振荡会伴随着金属吸收损耗。因此,等离激元效应能否在将激光体积变小的同时提高其性能是这一领域所必须回答的核心科学问题。
2017年,一项实验工作确证了在衍射极限附近及更小特征尺度下,等离激元效应可以全方面提高激光性能[52]。实验对约100余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进行了系统研究,给出了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各关键性能指标随尺寸变化的规律,并进一步将获得的特性规律与约100余组光学模式纳米激光对照样品进行对比,证明了等离激元效应可以使激光同时具有更小的物理尺寸、更快的调制速度、更低的阈值与功耗(图6)。实验上实现的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的模式体积可小至约0.01 λ3(λ为激光波长),比无等离激元效应的光学模式激光小约一个量级;同时其功耗与光学模式激光不同,可持续随其体积变小;在相同阈值情况下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具有更快的辐射速率,显示其具有更快的调制速率。

图6 200余组器件与对照样品系统实验证明,在衍射极限附近及更小特征尺度下,等离激元效应可以全方面提高激光性能[52] (a)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结构示意图(上)、模式场分布顶视图(中)和边视图(下);(b)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结构示意图(上)、模式场分布顶视图(中)和边视图(下),可以看到,(a)图中的光场分布比(b)图中的光场分布在空间上更局域;(c)等离激元纳米激光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的增益材料厚度与体积分布图;(d)等离激元纳米激光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的阈值随体积变化图;(e)等离激元纳米激光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的功耗随体积变化图;(f)等离激元纳米激光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的自发辐射寿命与阈值分布图[52]
这一实验解决了金属等离激元效应能否提高激光性能这一纳米光学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揭示了等离激元纳米激光在衍射极限下相较于光学激光的优势,为激光的进一步微型化铺平了道路[53]。
简而言之,相较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的腔损耗部分多出了金属吸收损耗,但是,由于等离激元效应的强光场限制,其辐射损耗可以比光学模式纳米激光小得多,因此,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的总的腔损耗可以小于光学模式纳米激光。通过激射模式中维持一个光子的激光激射的量子阈值定义,等离激元纳米激光中寄生性金属吸收损耗引起的阈值功耗(Pmetal)可以通过Pmetal=γmetal∙hv来估算,其中hv是纳米激光发射的单个光子的能量。一般的金属损耗速率约为1013—1014每秒,假设发射的光子能量hv为1 eV,我们可以得到等离激元金属损耗所对应的功耗仅约为1—10 µW[54]。
04
纳米HTH登陆入口网页
纳米激光可以在频率、空间和时间维度同时局域光场,因而具有小体积、低功耗、高速率、高功率密度等特点,在数据通讯、芯片上光互连、传感探测、生物医疗和超分辨成像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图7)[45]。

图7 纳米激光优势特性和相应应用领域[45]
在数据通讯和光互连领域,纳米激光能够进一步缩减激光尺寸,从而降低功耗,提高集成度和调制速度,帮助解决数据传输不断增长的能耗问题和芯片上光互连缺乏片上光源的“瓶颈”问题[45]。
在传感探测领域,激射增强等离激元共振(lasing enhanc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LESPR)可以大幅增强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在近场谱学、传感探测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55]。等离激元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探测器是表征和量化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重要工具,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光学生物传感器之一。激射增强等离激元共振探测器在具有极小模式体积的同时,通过增益补偿等离激元共振探测器中的损耗,进一步提高传感探测的灵敏度。例如在爆炸物分子探测中,激射增强等离激元共振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可以超过1 PPB(part per billion)[56]。
在生物医疗领域,等离激元激光可以被活细胞兼容,从而作为细胞内原位光源对细胞进行示踪或成像诊断[57,58]。更进一步,可以利用等离激元激光在激射时产生的热量,使激光周围产生蒸汽泡,进而对细胞进行杀伤,这一特点可以用于癌细胞的清除[57]。
在超分辨成像领域,等离激元纳米激光的受激辐射有望替代荧光分子的自发辐射,从而避免荧光分子的淬灭和光通量不足的问题,实现高通量快速实时超分辨光学成像[59]。此外,激光激射线宽远小于荧光分子的荧光线宽,为多通道超分辨光学成像提供了便利。
纳米激光的模式工程可以按需产生特定光场,比如涡旋激光、拓扑激光、魔角激光、奇异点激光等。通过近场或远场耦合,我们可以将纳米激光进行相位锁定,甚至可以控制每个纳米激光的偏振、相位和强度,这种协同本征模式工程可以实现对宏观激光场的前所未有的控制,从而催生一系列新型激光。
05
总结与展望
激光的微型化之路还将继续,以探索光场局域的极限及相关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原理。在应用层面上,实现纳米激光驱动的数据通讯和光电集成芯片仍是这一领域核心的研究目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实现室温、电注入纳米激光,并将其与光纤或者片上波导高效耦合。纳米激光在近场谱学、传感探测、医疗诊断和超分辨成像等领域的应用可能更易实现。这些方面的应用没有电注入等苛刻的微纳加工和材料调控的限制,只需将纳米激光按照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激射波长、结构构型等优化,以与具体应用系统兼容。纳米激光阵列及其远场应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兴领域,不仅有望实现高功率单模半导体激光,还可以按需定制激射光场以满足不同应用需求。
参考文献
[1] Einstein A. Phys. Z.,1917,18:121. (First printed in Physikalische Gesellschaft Zürich. Mitteilungen,1916,18:47)
[2] Purcell E M. Phys. Rev.,1946,69:681
[3] Lamb W E Jr,Retherford R C. Phys. Rev.,1947,72(3):241
[4] Casimir H B G,Polder D. Phys. Rev.,1948,73(4):360
[5] Jaynes E T,Cummings F W. Proc. IEEE,1963,51(1):89
[6] Drexhage K H,Fleck M,Kuhn H et al. Ber. Bunsenges. Phys. Chem.,1966,20:1179
[7] Kleppner D. Phys. Rev. Lett.,1981,47(4):233
[8] Goy P,Raimond J M,Gross M et al. Phys. Rev. Lett.,1983,50(24):1903
[9] Gabrielse G,Dehmelt H. Phys. Rev. Lett.,1985,55(1):67
[10] De Martini F,Innocenti G,Jacobovitz G R et al. Phys. Rev. Lett.,1987,59(26):2955
[11] Heinzen D J,Childs J J,Thomas J E et al. Phys. Rev. Lett.,1987,58(13):1320
[12] Yablonovitch E. Phys. Rev. Lett.,1987,58(20):2059
[13] John S. Phys. Rev. Lett.,1987,58(23):2486
[14] Yablonovitch E,Gmitter T J,Bhat R. Phys. Rev. Lett.,1988,61(22):2546
[15] Kurizki G,Genack A Z. Phys. Rev. Lett.,1988,61(19):2269
[16] Yokoyama H,Brorson S D. J. Appl. Phys.,1989,66(10):4801
[17] Bjork G,Yamamoto Y. IEEE J. Quant. Electron.,1991,27(11):2386
[18] Yamamoto Y,Machida S,Björk G. Phys. Rev. A,1991,44(1):657
[19] Yokoyama H,Nishi K,Anan T et al. Opt. Quant. Electron.,1992,24:S245
[20] Gordon J P,Zeiger H J,Townes C H. Phys. Rev.,1954,95(1):282
[21] Schawlow A L,Townes C H. Phys. Rev.,1958,112(6):1940
[22] Maiman T H. Nature,1960,187:493
[23] Holonyak N Jr,Bevacqua S F. Appl. Phys. Lett.,1962,1(4):82
[24] Quist T M,Rediker R H,Keyes R J et al. Appl. Phys. Lett.,1962,1(4):91
[25] Nathan M I,Dumke W P,Burns G et al. Appl. Phys. Lett.,1962,1(3):62
[26] Hall R N,Fenner G E,Kingsley J D et al. Phys. Rev. Lett.,1962,9(9):366
[27] Kroemer H. Proc. IEEE,1963,51(12):1782
[28] Alferov Z I,Kazarinov R F. Semiconductor Laser with Electrical Pumping (in Russian). Patent no. 181737 (priority as of 30 March 1963)
[29] McCall S L,Levi A F J,Slusher R E et al. Appl. Phys. Lett.,1992,60(3):289
[30] Painter O,Lee R K,Scherer A et al. Science,1999,284(5421):1819
[31] Huang M H,Mao S,Feick H et al. Science,2001,292(5523):1897
[32] Bergman D J,Stockman M I. Phys. Rev. Lett.,2003,90(2):027402
[33] Oulton R F,Sorger V J,Zentgraf T et al. Nature,2009,461(7264):629
[34] Hill M T,Marell M,Leong E S P et al. Opt. Express,2009,17(13):11107
[35] Noginov M A,Zhu G,Belgrave A M et al. Nature,2009,460(7259):1110
[36] Ma R M,Oulton R F,Sorger V J et al. Nat. Mater.,2011,10(2):110
[37] Berini P,De Leon I. Nat. Photon.,20126(1):16
[38] Ma R M,Oulton R F,Sorger V J et al. Laser Photonics Rev.,2013,7(1):1
[39] Hill M T,Gather M C. Nat. Photon.,2014,8(12):908
[40] Gwo S,Shih C K. Rep. Prog. Phys.,2016,79(8):086501
[41] Eaton S W,Fu A,Wong A B et al. Nat. Rev. Mater.,2016,1(6):1
[42] Wang Z,Meng X,Kildishev A V et al. Laser Photonics Rev.,2017,11(6):1700212
[43] Chou Y H,Chang C J,Lin T R et al. Chin. Phys. B,2018,27(11):114208
[44] Wang D,Wang W,Knudson M P et al. Chem. Rev.,2017,118(6):2865
[45] Ma R M,Oulton R F. Nat. Nanotechnol.,2019,14(1):12
[46] Ning C Z. Adv. Photon.,2019,1(1):014002
[47] Stockman M I. Advanced Photon.,2020,2(5):054002
[48] Liang Y,Li C,Huang Y Z et al. ACS Nano,2020,14(11):14375
[49] Azzam S I,Kildishev A V,Ma R M et al. Light:Sci. Appl.,2020,9(1):90
[50] Deka S S,Jiang S,Pan S H et al. Nanophotonics,2020,10(1):149
[51] Ma R M,Wang S Y. Nanophotonics,2021,10(14):3623
[52] Wang S,Wang X Y,Li B et al. Nat. Commun.,2017,8(1):1889
[53] Noginov M A,Khurgin J B. Nat. Mater.,2018,17(2):116
[54] Ma R M. Nat. Mater.,2019,18(11):1152
[55] Zhang Z,Nest L,Wang S et al. Photon. Res.,2021,9(9):1699
[56] Ma R M,Ota S,Li Y et al. Nat. Nanotechnol.,2014,9(8):600
[57] Galanzha E I,Weingold R,Nedosekin D A et al. Nat. Commun.,2017,8(1):15528
[58] Martino N,Kwok S J J,Liapis A C et al. Nat. Photon.,2019,13(10):720
[59] Gao Z,Wang J H,Song P et al. Adv. Mater.,2020,32(9):1907233
(参考文献可上下滑动查看)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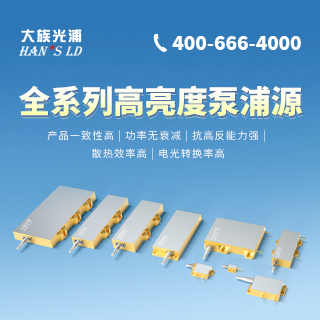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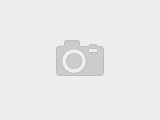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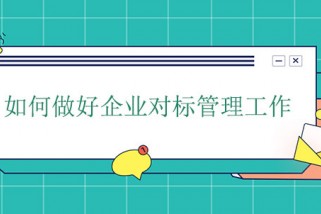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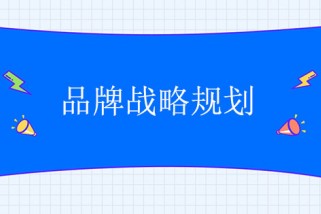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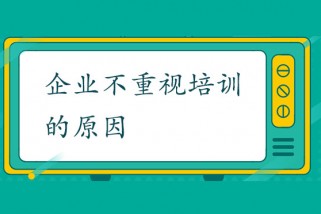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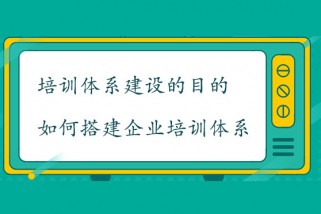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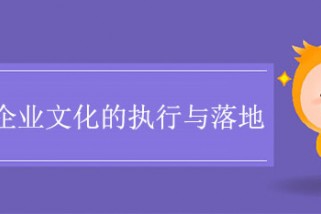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