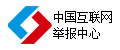这是一个未来战争的场景:交战双方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突然,空天导航卫星被摧毁,信号随之中断。然而,战场并没有沉寂,部分高新武器火力依然按照计划击中既定目标。 这精确打击的背后,离不开自主导航系统中一个叫作“激光陀螺”的核心器件。 为了让激光陀螺“起舞”,在湘江之畔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43年的矢志坚守和披肝沥胆,让我国的激光陀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绽放出耀眼的强军之光。 他们,就是国防科大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 激光陀螺是什么?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大放异彩,令世人瞩目。而让“战斧”巡航导弹实现“千里点穴”功能的核心器件,就是激光陀螺。被誉为茫茫海天“定位神器”的激光陀螺,自问世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国防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时间追溯到1960年,美国率先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后,马上开始激光陀螺的研制。由于激光陀螺与传统机械陀螺相比,启动快、动态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可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等领域的高精度惯性导航,因此世界各国纷纷跟进,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场导航技术的革命。但是,由于涉及众多前沿技术和先进工艺,我国研发工作曾一度停滞,仅有美国等少数国家还在坚持。
60年代末,美国研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并于70年代末期在战术飞机和战术导弹上试验成功,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一轮激光陀螺的研制热潮。 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敏锐地捕捉到激光陀螺巨大的潜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971年,在他的指导下,国防科大成立激光教研室,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之路。 当初,我国也有10多家单位开展这项研究,最后绝大多数都因基础工艺过不了关而放弃。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团队负责人高伯龙说。 刚开始研制激光陀螺时,高伯龙和他的同事连制作激光器用什么材料都不知道。一次,他听说大理石膨胀率较低,可以选用。为节省开支,高伯龙就推着平板车到长沙火车站工地去捡废料,一次又一次,风雨无阻。
一天,当高伯龙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他的老伴儿心疼地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何苦?”他淡然一笑:“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如果现在再不抓紧,什么时候能赶上?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
高伯龙患有哮喘病,胆囊和心脏也有问题,常年靠超剂量服用药物控制。有一年,组织上送他进京治疗,他嘱咐大家:“我这一去不知会怎样,但你们一定要坚持搞下去,给国家有个交代。”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为了打破国外垄断,让中国的激光陀螺绽放光彩,整个团队铆足了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鏖战,1994年11月8日,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国防科大诞生,向全世界宣告:继美俄法之后,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够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面对鲜花和掌声,他们没有陶醉。龙兴武教授毅然接过老师高伯龙手中的接力棒,带领团队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发起冲锋。为使激光陀螺走出实验室,他们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研制出一套套设备、填补了一项项国家空白,完成了激光陀螺迈向工程化的华丽转身。经过43年的发展,团队已成为我国激光陀螺研究领域的国家队和主力军,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个第一。
面对大量空白,团队从零开始,研制初期进展十分缓慢。高伯龙引领团队另辟蹊径,提出了全新的技术路线,整理撰写了《环形激光讲义》,成为我国该领域的奠基之作,为后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依据。
激光陀螺是一项高精尖科技,一个几十克的陀螺,却集中了光学、材料学、化学、电子学等五大领域数百项技术,这既需要理论的攻关,又需要技术的攻关。因此,团队中无论是两鬓斑白的老教授,还是归国不久的年轻博士,既是理论研究领域的“白领专家”,又是工程一线操作的“蓝领工人”。在研制工程化样机时,最大的“拦路虎”是被称为“关键技术之首”的镀膜。当年,由于我国工艺水平落后,最难的时候一年只能镀几个陀螺,突破不了这道难关,就无法实现大规模装备生产。为了突破工艺技术这道难关,高伯龙等人不得不放弃多年钟爱的理论研究,转向专攻基础工艺,向膜系设计这一难关发起冲锋。当时国内计算机还未普及,没有现成的软件可用,他们就自学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完成了膜系设计。
超精密光学加工是激光陀螺研制的又一个“拦路虎”。在激光陀螺的研制过程中,超光滑表面腔镜的制备困难重重,美国花了很多年才将这一问题解决,而且一直作为核心技术秘密限制传播。在我国,先后有10余家研究单位卡在了超精加工工艺上,纷纷选择了放弃。
“从头再来!”金世龙教授斩钉截铁地说。他舍弃了原本从事的光学理论研究,来到加工生产一线,从最普通的工艺入手,拜工人为师,潜心一线加工。 每次攻关都是严峻的挑战,每次突破都是巨大的跨越!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攻克了一系列工艺难题,终于掌握了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腔镜光学加工技术。科学是一座无形的山峰,攀登需要付出智慧和汗水。在激光陀螺技术创新团队攻关的征程中,留下了许多顽强拼搏的足迹和身影。激光陀螺在应用过程中面临外围控制电路复杂、体积较大的问题。如何制造体积小、精度高同时还要像“傻瓜相机”一样加电就可直接使用的激光陀螺仪这一难题,摆在研究人员面前。
把“傻瓜”和“精细”相统一,面临的第一问题是:如何把电路小下来,小到和陀螺的尺寸相匹配?有人说,干嘛这么较劲,大就大点呗!但罗晖教授却说:“陀螺仪大一寸,导弹就大一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做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晖把近5年所有生产的陀螺测试数据都打印了出来。那段时间,他整天扎在数据纸堆里,对数据一一进行分析整理、仔细对比,一干就是9个月,终于找到了规律,缩小了尺寸,提高了精度。 43年默默无闻的背后,饱含着“陀螺人”的默默付出。高伯龙说:“虽然我们没钱,但不能缺志气。”没有场地,他们就将一间废旧的食堂改造成实验室,因为科研需要还要封闭起来。为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实验室里没有安装空调,一到夏天,实验室就变成了大闷罐,大家在里面挥汗如雨,通宵达旦地干。到了冬天,实验室就成了大冰窖,阴冷潮湿,很多人手脚长满了冻疮。
1994年工程化样机通过国家鉴定的那天晚上,高伯龙和他的同事难得轻松地从实验室回家。走在校园宁静的路上,他突然发现路边多了一栋新楼,不解地问:“这里什么时候多了栋新楼?”同事哈哈大笑起来:“你才发现啊?这栋楼一年前就盖起来了。”
这些年来,无论是八旬高龄的老院士、老教授,还是刚刚博士毕业的80后,都把实验室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研制工作最艰难的时期,他们每天在实验室超过15个小时,几乎每年春节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团队成员平均每年加班1500个小时,多的超过2000个小时。团队年轻的博士小曲,孩子才出生两天,就又回到了实验室。2008年初,还有一周就到传统的新春佳节。那年的冬天格外冷,湖南出现了严重的冰灾。为了完成车载试验,他们下午抱着设备从长沙出发,直奔南岳衡山。受冰灾影响,200多公里路程汽车足足开了6个多小时,他们到达山脚下已是半夜。刚一下车,刺骨湿冷的狂风冻雨就将张博士的帽子卷飞出几十米。就这样,大家手拉着手,顶风冒雨爬到山顶祝融峰上开始试验。
直到凌晨两点完成试验后,他们在山上找到一家宾馆抓紧整理数据,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于博士开门一看,几名保安站在门外——原来,宾馆服务员见他们深夜抱着箱子、抬着柜子,进进出出、神情兴奋,误把他们当成了窃贼。整理完数据,为测量海拔和纬度对试验系统的影响,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连夜下山转战广州,途中,由于雾气太大,能见度只有几米,他们依然冒险继续赶路。这期间,谢元平副教授为了不影响试验进度,强忍着颈椎错位带来的疼痛,冒着高位截瘫的危险,戴着颈托钻进狭窄的试验空间,一干就是两天两夜,直到试验结束才被人扶出来。
43年来,由于保密需要,团队成员的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由于攻关进程紧张,他们分不出精力准备评奖材料,43年来只评了3次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没有论文和获奖成果的支撑,很多专家做了无名英雄。一些地方单位愿意年薪百万聘请,但为了让自己的陀螺绽放异彩,也都被他们婉拒,始终心无旁骛干事业、一心一意搞科研。
当有人问到,为何43年来团队能够默默无闻,始终矢志不移。国防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秦石乔坚定地说:“面对国家利益,其他都是浮云。让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战斗力,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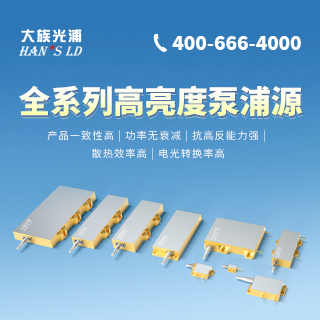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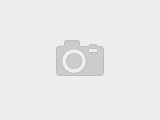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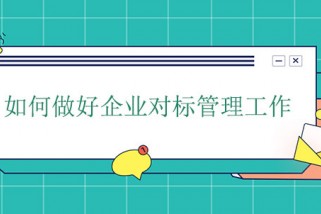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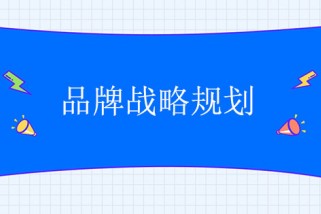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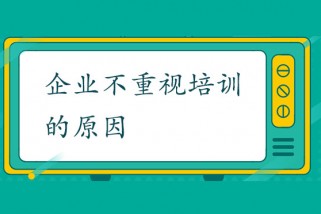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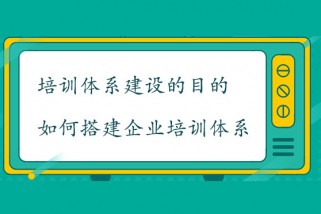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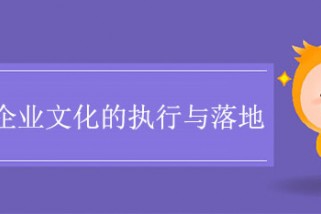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